资讯分类
又不是没演技,她怎么就不红啊 -
来源:爱看影院iktv8人气:987更新:2025-09-11 10:04:54
上周五,白玉兰奖正式发布入围名单,张颂文凭借《狂飙》的出色表现意外落选,这一结果在网络上掀起热议。随后有媒体披露,实为剧组未提交报名材料所致,而非奖项本身存在遗漏。面对这一舆论风波,不少观众自发在社交平台为张颂文颁发"最佳热度贡献奖",以表达对其作品影响力的认可。

图源:微博@玲娜贝儿的野生妈咪,其制作水准堪称高超。随着相关话题登上热搜,越来越多实力派演员被提及,其中包括高叶、杨蓉、辛柏青、海清以及《三体》中的女主人公王子文。王子文演绎的叶文洁层次分明,这位历经时代动荡的女性对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既有天真无邪的一面,又暗藏锋芒,更难诠释的是她内心的冷酷与柔情交织的矛盾感。

然而,她在新作《温柔壳》中饰演的抑郁症患者觉晓却彻底颠覆了我对她的既有印象。

自出道以来,王子文凭借小荧屏中的角色获得广泛关注,其中《三体》中沉着冷静的叶文洁和《欢乐颂》里俏皮可爱的曲筱绡尤为深入人心。许多观众正是通过这两个角色了解她,从而产生了她本人性格与角色相似的误解,认为她具备刁蛮毒舌的作精特质。

图源来自《欢乐颂》。她过往塑造的角色多以真实细腻见长,而非常见的偶像剧风格。初入影视圈便参与了许鞍华导演的文艺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展现出了独特的成熟气质。早年接受舞蹈与体操专业训练,学生时代被经纪公司选中赴韩国接受歌手培训,后因组合解散转向演艺道路,陆续接演各类配角。随着近年来事业逐渐好转,她在恋爱综艺中坦承自己育有一个近十岁的孩子(生父身份尚未明确),这一坦白引发了广泛社会讨论。

可以预见,经历了人生轨迹发生重大转变、多年间兼顾事业与育儿责任的磨砺,这位演员必然在内在力量与心理韧性层面获得显著提升。这些沉淀与积累,自然转化为其表演艺术的深度与广度。在年初的平遥国际电影展上,她凭借在《温柔壳》中细腻入微的诠释斩获最佳女主角殊荣。影片于上周五公映后,持续保持着影展期间的口碑热度,并同时斩获最佳导演与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

图源:微博@王子文工作室。在众多赞誉中,最被提及的评价莫过于“王子文应当重返大银幕”。对此我深表认同。影片讲述觉晓自幼被母亲遗弃,父亲行踪成谜,因执着追寻母亲的信念,她逐渐陷入抑郁深渊,最终在小姨(咏梅 饰)将其送入精神病院后,表现出自残倾向。

觉晓的沉沦折射出原生家庭的裂痕。她执着追寻的并非某个人,而是一个自我证明的出口——证明自己并非被世界遗弃。然而当现实一次次将她推开,这份执着最终沦为对命运的无声控诉。生命成为她唯一的筹码,于是选择以极端方式反抗,试图挽留小姨最后的温情。人在彻底绝望时,往往陷入一种冰冷的麻木,不再期待黎明,连言语都变得沉重。那些将情绪外化为嘶吼与泪水的表演,反而让真实的绝望显得苍白。王紫文演绎的觉晓,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这种静默的崩溃:在被同院病患戴春(尹昉 饰)从割腕的边缘救回后,她看清了小姨更深的疏离,整个人如被抽去灵魂般萎顿,彻底放弃挣扎。

表面看来,她始终保持着平静的假象。每当戴春试图与她交谈,她总会突然尖叫,将对方吓退;平日里也总独自坐在院落,用沉默消磨时光。然而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眸,却悄然泄露了内心的深渊——满溢着难以言说的绝望。正如画家与导演所深谙,人物的眼神往往是最具表现力的细节。那些善于运用眼神的演员,在镜头特写时即便面对怼脸镜头也能从容应对,终将成为大银幕上的主角。相较之下,男主戴春则始终散发着躁动的气息。清晨的庭院里,他总是最早开始晨练的人;当病人突发晕厥时,他第一个冲上前去施救;甚至故意藏起药物来捉弄护工,这些举动都彰显着他与觉晓截然相反的性格特质。

他脸上总带着温和的笑容,若非四肢偶尔出现夸张的摆动,外界很难发现他患有精神疾病。这并不代表尹昉的表演存在瑕疵。相较之下,许多影视作品对精神病人的描绘存在猎奇倾向,这种扭曲的呈现方式反而强化了社会对这类群体的偏见。王沐导演创作该片的初衷,正是希望公众能够以平等、理性的视角审视精神病人——他们除了在发病时难以控制行为,日常生活中同样需要进食、如厕、经历情绪波动,也拥有对爱欲的正常需求(当然严重病例存在特殊性)。

尹昉在表演中精准呈现人物本质,展现出扎实的演技功底。值得注意的是,戴春所患并非单纯抑郁症,而是更为复杂且普遍存在的双相情感障碍(俗称躁郁症)。这种疾病的成因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其父同样患有该病症。双相情感障碍的特点在于症状呈现两极分化,患者可能在狂躁期表现出异常亢奋,转瞬又陷入深度抑郁;更常见的是两种症状交替出现,甚至混合发作,这种状态可能诱发不可预知的暴力行为。

试想,戴春在怎样的环境中度过童年。随着母亲因不堪重负选择离开,家中仅剩他与弟弟(白客饰演)相依为命,而年迈的父亲正饱受病痛折磨,三人在困顿中艰难维系着破碎的家庭。

面对情绪困扰时,许多长辈往往认为这是生活常态,难以意识到及时就医的重要性。即便有所认知,社会对心理疾病的偏见仍可能使他们选择沉默。在戴春的故事中,父亲则选择用酒精来麻痹痛苦,本就复杂的心理状态逐渐失控,病情愈发严重。影片虽未直接呈现暴力场景,但通过戴春后背的疤痕与每次见父亲时的本能戒备,我们得以窥见童年时期他如何以身体为盾,默默承受着家庭暴力的伤害,只为保护年幼的弟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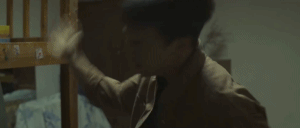
戴春的双相情感障碍源于家族遗传,更与父亲的暴力息息相关。对他而言,家如同吞噬光明的深渊,无法给予温暖与安宁。他无法责怪任何人——母亲背负着难以言说的隐忍,父亲自身也陷于无法挣脱的困局。戴春只能将命运归咎于无常的际遇,而觉晓同样深陷命运的漩涡。当两个被苦难缠绕的灵魂相遇,彼此成为了对方在绝望中看到的微光。干涸的心灵荒漠里,偶然遇见一片微光闪烁的绿洲,随着羁绊加深,这片绿洲逐渐壮大,终在相互滋养中生长出名为希望的嫩芽。
rex
这份情感既令人动容,又带着刺骨的冷峻。动人之处在于,爱情成为了两个陷入绝望的灵魂相互拯救的契机。最初戴春接近觉晓,只是源于本能的好奇——她天生的美貌与入院后突如其来的自残行为令所有人无法忽视她的存在。而戴春未曾察觉,觉晓平日里若有若无的温柔,竟与他早已离开的母亲如出一辙,正是这份似曾相识的暖意,让他在病发时的狂躁中逐渐迷失自我,沉溺于守护觉晓的执念。

觉晓赋予了戴春自我关爱的勇气。然而,戴春历经挣扎逃离了疗养院,最终仍选择重返院中,守候在觉晓身旁。而戴春则为觉晓寻得了尘封已久的真相——‘我从未被这个世界所遗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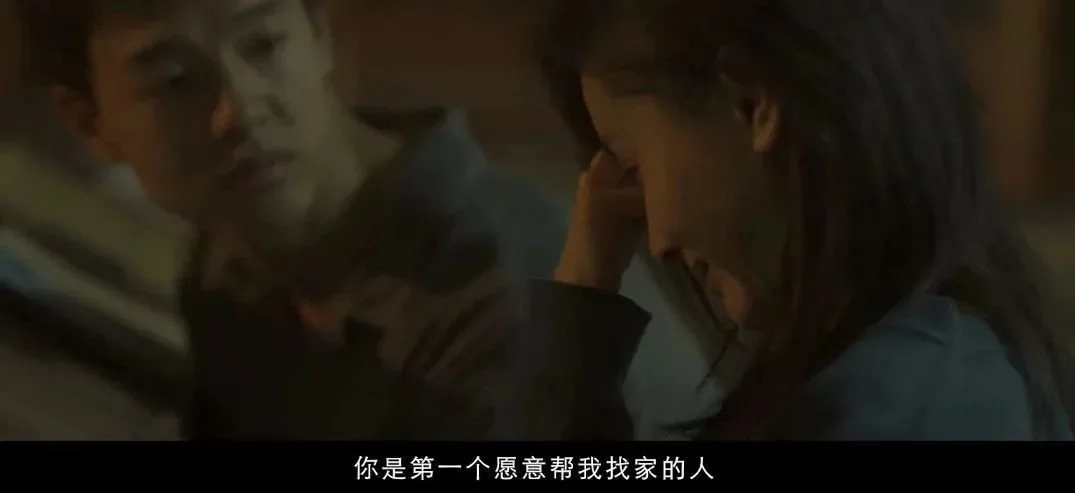
戴春并未因困境而放弃对觉晓的守护,当他自己的鞋子遗失、双脚被磨出鲜血时,途经鞋摊却只顾着为觉晓选购一双新鞋。这种无私的付出令他仿佛将觉晓视若珍宝般呵护。若要探讨精神疾病患者的爱情与常人的差异,或许就在于这份纯粹的执着——他们的情感表达毫无保留,喜悦时必欲牵手共舞,关怀时宁愿送对方一个苹果或一瓶可乐。正是这份直率的爱意,成为他们与常人唯一能并肩而立的支点。


这份爱轻盈如初遇时的悸动,却深沉似唐诗中蕴含的意境,让身处黑暗的他们得以窥见破晓的微光。在监护人的默许下,他们攥着出院同意书重新踏入尘世,试图在生活的赛道上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当现实的残酷逐渐浮现,这份爱便显露出锋利的棱角——即便他们竭尽全力奔跑,前行的每一步仍比常人更加艰难。社会尚未真正准备好接纳他们,仅仅是一道就业门槛,便布满将他们拒之门外的暗礁。戴春和觉晓用尽所有力气,才得以在边缘地带找到生存缝隙,成为外卖骑手或美甲师。这些工作虽维持着基本生计,却常伴随顾客的苛责,维系着摇摇欲坠的体面。而这样的处境,已属于精神病人重返社会后较为幸运的案例。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像周依然饰演的小马般,他们被层层筛选后只能从事替代性较强的岗位,如同超市理货员,然而即便如此,也难以长久维系——最终仍难逃被辞退的命运。

人们往往将目光投向小马这类个体,而非反思工具理性社会带来的冷漠与不公。更可能借助"工作无分贵贱"的陈词滥调,将"变相歧视"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这种逻辑本身便充满矛盾。当效益成为社会最高准则,各类职业被冠以标签并赋予不同价值,工作本身的平等属性便被彻底消解。戴春、觉晓与小马所象征的群体,正是这套体系下的被边缘化者。他们承担着与他人相当甚至更多的劳动量,却仅获得低于平均水平的报酬,反而被利益集团当面质问:"社会多平等,是你自己能力不行罢了"。这番话无异于强盗逻辑,彻底颠倒了是非。若他们敢于憧憬更美好的生活,试图像他人一样组建家庭,势必会遭遇旁人斥责:"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妄想养育下一代?"

他们的不幸并非源于缺乏幸福的资格,而是社会系统性地剥夺了这一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戴春和觉晓所面临的困境远比表面更为复杂——除了物质贫困,更深层的焦虑在于无法预知孩子是否会继承家族的疾病基因,从而陷入新的不幸循环(双相情感障碍具有较高的遗传倾向,且存在隔代遗传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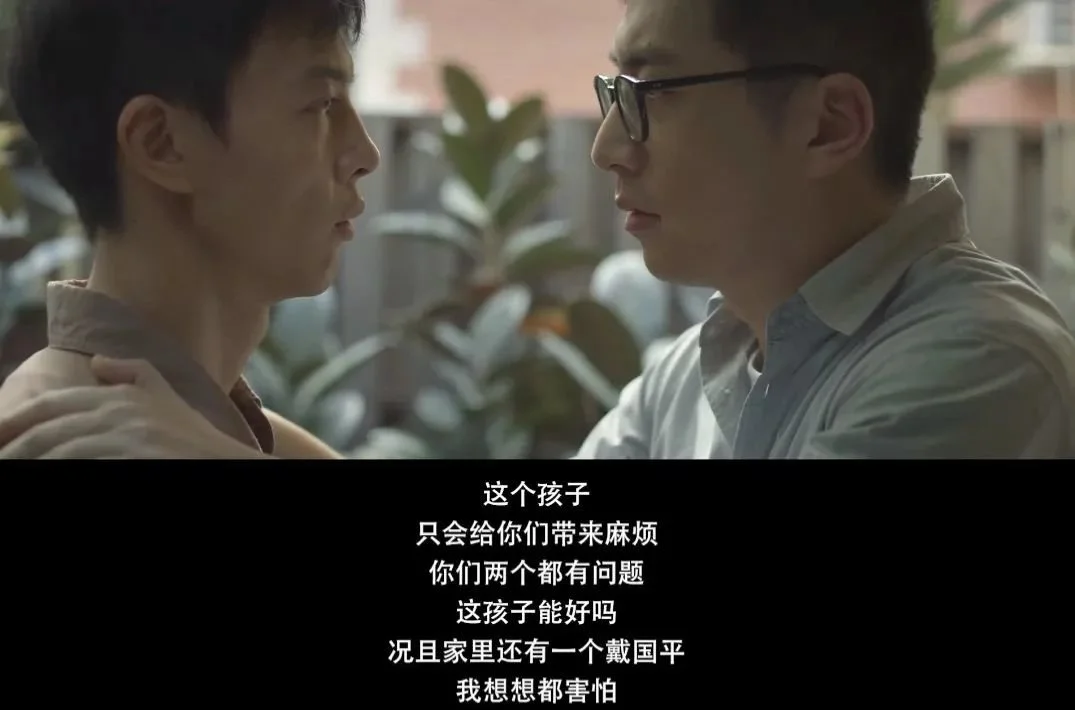
然而,若仅因这一现状便否定他们的生育权利,岂非体现了社会的短视?这恰似一种疾病发生时,人们倾向于治疗患者本身,而非探究病因、根治病灶。在现有医疗体系难以触及根本问题的现实下,若不思考社会应如何构建支持系统,让微弱的希望出现时,不至于让局势失控。却直接以粗暴的口吻宣称:你们生不得。然而,我亦能理解剧中戴春之弟为何反对生育。当社会支援尚未健全,那微弱的希望降临到个体身上时,便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重负。于是,戴春与觉晓刚刚初现的曙光,再次被笼罩在暗夜里。

《戴春病情复发入院》这部影片的结局始终未向观众揭晓主角们最终是否获得幸福,但透过细腻的叙事,导演的立场已然清晰:真挚的情感成为支撑彼此前行的唯一力量。剧情节奏的争议亦由此而生,爱是否真的如导演所言那般坚韧?相较于同为精神病题材的《绿洲》,李沧东的作品显然更显冷峻克制,其对爱情的诠释犹如荒漠中一抹难以捉摸的绿意。尤其当与《温柔壳》对比时,《绿洲》中爱情的纯粹性甚至更胜一筹。例如片尾男主角在被送入监狱前逃离看守所,耗费巨大精力并非为了重逢女主,而是执着于砍掉女主窗外枯树上的所有枝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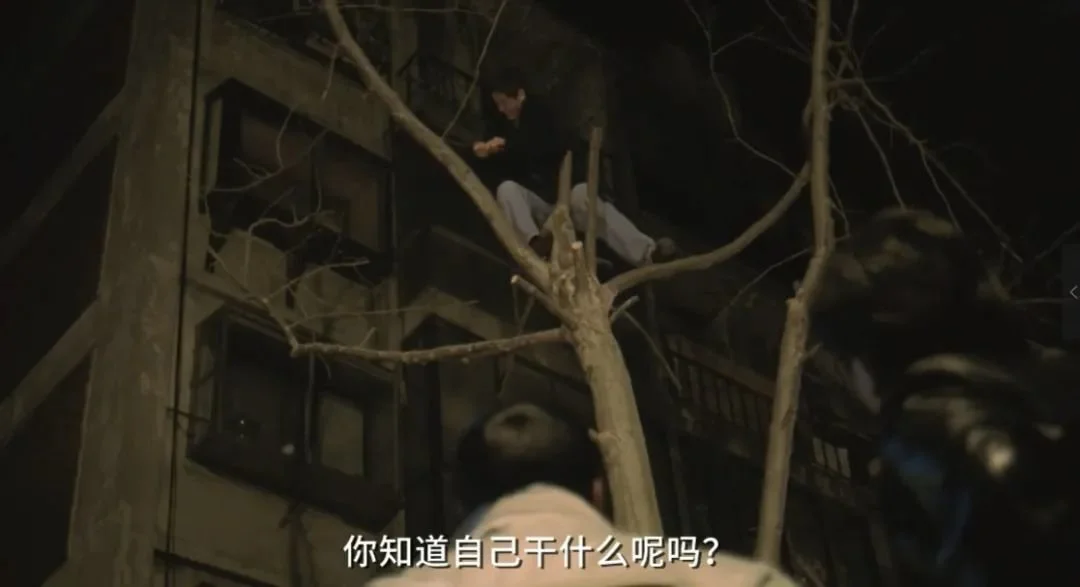
出于对女主内心脆弱的理解,男主立下誓言:若自己不在身边,便让她的恐惧得以消散。这份深情令人动容,却也引人深思——当爱情的开端与伤害紧密相连,究竟该如何定义其真谛?

李沧东所描绘的,实则是社会边缘群体被时代忽视的爱欲困境。尤其是像女主这般拥有肢体障碍的极少数个体,其内心压抑至近乎病态的渴望,竟会扭曲到对施暴者产生迷恋。尽管《温柔壳》与《绿洲》在叙事态度上存在差异,但二者内核却高度趋同——皆以纯爱的表象下潜藏的真相为切口,揭示精神病人被社会层层挤压的生存状态。他们被制度性地放逐、被文明所遗落,呐喊无处安放亦无法选择,最终只能在彼此的孤独中构筑最后的精神避难所。导演并非在讴歌爱情,而是在为这些被世界遗忘的灵魂保留一束微光。这光并非虚无缥缈,当戴春陷入精神崩溃时,觉晓始终挺身而出,用瘦削的身躯为他构筑临时的庇护空间。在那些短暂的相拥时刻,戴春的呼吸逐渐平复,意识重返人间,印证了人性微光即便微弱,也足以照亮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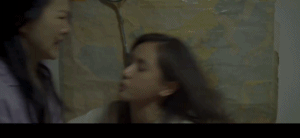
他们并非缺乏融入社会的能力。正如电影《温柔壳》所借喻的——精神病人恰似蜕壳期的螃蟹,需要一片避风港静待新壳成型。然而现实却始终拒绝提供这样的空间,这残缺的外壳便永远无法完整。于是只能拖着支离破碎的躯体,在生活的浪潮中被冲刷出遍体鳞伤。渴望前行却始终困顿于原地。若你真心想有所作为,就不该质问他们为何步履缓慢,也无需催促他们奔跑。试着为他们留些喘息的余地。纵使痛苦依旧,生存仍显艰难,问题尚未解决,但或许因此能避免一个彻底绝望的灵魂。只要尚未熄灭希望的火光,便仍有破茧成蝶的可能。长出属于自己的外壳,找到生活的出路。
最新资讯
- • 《疯狂的麦克斯:狂暴女神》特辑 安雅锤哥见证史诗 -
- • 陈乔恩晒与谢娜合照 二人cos《破产姐妹》造型颜值超高 -
- • 《谈判专家》预告海报双发 刘德华演绎底层之苦 -
- • 仲野太贺与木龙麻生进出公寓 二人共度三天两夜 -
- • 《扫黑·决不放弃》上映 肖央余皑磊曝“真面目” -
- • 《最佳利益》开播获好评 天心自称戏里戏外反差大 -
- • 《疯狂的麦克斯:狂暴女神》预告 揭秘安雅复仇之路 -
- • 2024端午档总票房破2亿 《扫黑·决不放弃》领跑! -
- • 陈羽凡被曝开豪车载女友出门 违规并线与后车发生剐蹭 -
- • 《大雄的地球交响乐》特辑 开启哆啦A梦音乐之旅 -
- • 时代峰峻就时代少年团亲属隐私权遭侵害发声明 -
- • 拒绝内耗!从跟胡歌高圆圆一起《走走停停》开始 -
- • 张婧仪进组不小心上错车 大喊“我上错车啦”超可爱 -
- • 是枝裕和新片发布感谢坂本龙一:他的配乐不可或缺 -
- • 争论不休,《美国内战》是“寓言”还是“预言”? -
- • 《扫黑·决不放弃》:这回力度不一样了 -
- • 范丞丞《奔跑吧》最新路透 cos半人马综艺感拉满 -
- • Angelababy《奔跑吧》最新路透 古装造型仙气满满 -
- • 张若昀到达襄阳进组《庆余年2》全黑look引期待 -
- • Ella陈嘉桦身穿爱心印花T恤 笑容灿烂元气满满 -